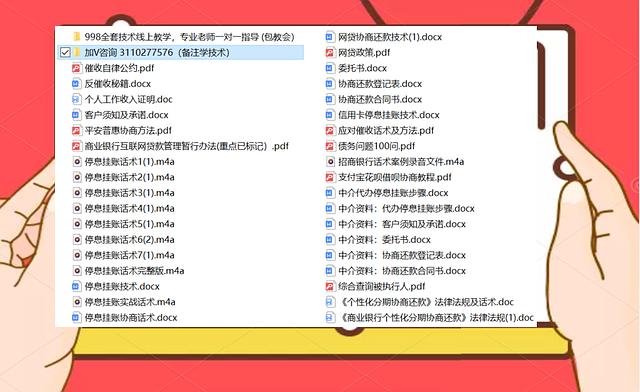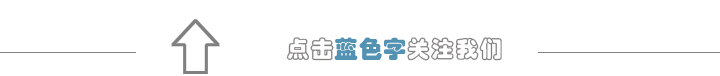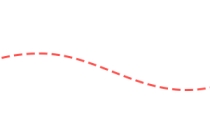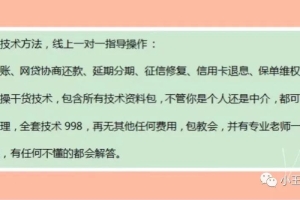贷款减免与利息挂账
宁波银行:储江南
:jiangnan_chu
为尽量降低银行债权的损失,或尽速处置完成不良贷款,债权银行与债务人达成部分清偿的方案在实务上甚为常见。在具体操作上,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达成,一是债权减免(下称“减免”),二是利息挂账(下称“挂账”)。减免其实就是民法上“免除”的概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债务人之债务。而挂账通常是指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且因银行内部或外界的因素,该贷款本金及利息亦不能在短期内获得偿还;为财务管理上之便利,银行对该贷款余额不再做计息处理,但贷款本金及先前产生尚未归还的利息仍记在原借款人名下。故,挂账本质上是一种会计上的处理方法。本文拟从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入手,结合法律规定、监管政策、司法判决及实务经验,对两者在实践中的运用做出整理、比较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适用建议。
一、区别与联系
从前述之定义中,即可得出减免与挂账之主要区别与联系,分述如下。其一,性质上,减免是单方法律行为,需由债权银行向债务人做出意思表示,具有对外性;而挂账纯系银行的账务处理,操作上与债务人无涉,似仅具内部性。唯应注意的是,银行既同意做减免,其中对债务人必另有所图,为重新明确债务人之义务,故实务中减免仍多采书面协议之形式,将单方行为变成双方行为甚至多方行为;挂账的操作亦不例外,除在实质意义上适用于前述道理外,理由还在于形式意义上,即借助书面形式将挂账原本的内部效力显露于外,以对债务人之债务履行产生实际影响。更需引起重视的是,实践中的减免与挂账虽多用书面协议,但在文字言语的表述上却大相径庭。个中差异,留待后述。
其二,对象上,减免针对的可以是主债务人的主债务,也可以是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而挂账的对象仅能是主债务人之主债务。因担保人并未在债权银行开立了专门的贷款账户,其根本无账可挂。
其三,效果上,减免乃债权消灭之原因,会导致债权本身全部或部分实质上的消灭,债务人与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局性的终止;挂账仅是会计上做停息处理,银行对债务人法律上的债权未受任何影响。即便是银行系统上已自动停息,但也不表示银行不能就停息处理后所产生的利息向债务人进行主张。
其四,适用上,减免和挂账分属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既可同时使用,亦可分开使用,互不羁绊,在适用的先后顺序上也并无讲究。具体说来,针对同一笔债权,若银行做出减免的动作时,可以同时选择在账务上做挂账处理,亦可事后再做,甚至不做;若银行走挂账的路径,则可以同时选择做债务减免,抑或不做。
二、法律与监管
商业银行能否享有自主决定的债权减免权利,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及政府对银行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在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银行被定位为贯彻、执行国家意志的金融机构,所有信贷收支必须按照规定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开展业务均需遵照国家政策,并无实际自主经营之权利。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曾在198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下称“银行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无权豁免贷款。”按字义理解,这里的“任何单位”自应包括银行,而“贷款”则包含本金与利息。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除国务院批准外,银行不得减免债权。这是从行政法规的高度做出的禁止性规定。
伴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银行的定位也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在1995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称“商业银行法”)中明确将“商业银行”定义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且,《商业银行法》也未如《银行管理条例》般明令禁止银行不得减免债权。而之所以对该问题,不着笔墨,究其缘由,依笔者揣度,应是立法者认为商业银行既以剥离所谓计划性和政策性的外衣,被赋予自主经营之权利,理应可享有自主决定的债权减免权利,毋庸赘述。不过彼时,《银行管理条例》虽实质上已被效力层次更高的《商业银行法》取代,唯其在形式上被正式废止,要待到2001年的10月份(参见:国务院令第319号《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综上,就目前的法律法规层面,并无禁止银行债权减免的规定。但同时银行业亦属于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故就减免一事,尚需考虑是否有部门规章或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特殊限制。从笔者的检索结果来看,监管部门对该减免事项始终持保守态度。早在198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对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参看:《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不得自行减免贷款利息问题的复函》银复[1988]85号),即依据《银行管理条例》之规定,指出“除法规、政策另有规定者外,任何单位(包括金融机构)都不得豁免贷款本金,不得放弃收取贷款和利息,不得减免贷款利息”。此复函为部门规范性文件,迄今仍然有效,尽管作为其参考依据的《银行管理条例》已被废止。之后,在《商业银行法》实施的第二年,中国人民银行以《商业银行法》为根据,制定颁布了对商业银行具有广泛影响及深刻意义的《贷款通则》。耐人寻味的是,《贷款通则》却并未承继《商业银行法》对债权减免的开放态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贷款通则》第十六条规定:“除国务院决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其第三十七条规定,针对不良贷款的催收,贷款人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豁免贷款。故,《贷款通则》又从部门规章的层次禁止商业银行可自主减免债权,且无论该贷款分类系处在不良还是非不良。
至于利息挂账,因仅涉及商业银行内部会计上做停息之处理,不会对银行债权造成实际上的减免,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应没有干预的必要。不过,《贷款通则》第十六条禁止的列举项里依然包括了“停息”的动作。再看其第三十七条,对于不良贷款只是规定不得豁免,并无提及停息。依照体系解释,《贷款通则》似乎是针对非不良类贷款与不良贷款做了区分处理,对于前者原则上禁止减免与挂账,对于后者仅禁止减免而已。这种解释或许可以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利息挂账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性。
三、裁判之观点
我国的银行业或者是金融业长久以来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存在着较松裁判尺度与较严监管标准的剪刀差。这为所谓金融创新预留了制度与操作上的空间。贷款减免亦不例外。正因法律法规上没有禁止性规定,故司法实务上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免操作普遍持肯定性意见。
稍有争议的是前述《贷款通则》的规定对司法裁决的影响。各级各地法院观点并不统一。如在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振祥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书中(2014桦商初字第167号),法院认为“还款协议原告虽然放弃了部分本息,客观上致使利益有所减损,但是对其享有权利的合法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贷款通则》第十六条虽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但该条款并非强制性规范,且该通则系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原告关于杨中元私自为李振祥减免借款本息,违反《贷款通则》以及《桦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应属无效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而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平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四川雪山实业有限公司、党正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绵民初字第117号)中指出:依照《贷款通则》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未经国务院批准,贷款人不得豁免贷款。除国务院批准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贷款人豁免贷款”的规定,由于该(债务免除的)《会议纪要》并未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故不具有减免四川雪山公司在平武信用社贷款的效力。随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265号)及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7川民申1847号)当中亦认可了这种观点。唯在此案被申请再审至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院在其民事裁定书中(2017最高法民申4342号)调整了论证的角度,其不再适用《贷款通则》之规定,而是认为“案涉贷款余额之减免需作为债权人的平武农商行以明确、确定之方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平武农商行于《会议纪要》中同意原则上对四川雪山公司按贷款全部减免的原则开展工作,有关全部减免四川雪山公司未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尚未达到明确、确定的程度。”如按反面解释,最高院似认为债权银行只要能做出明确及确定的减免债权意思表示,贷款减免的效果即可达成,《贷款通则》之规定在司法上不必斟酌。
笔者赞同最高院之观点,理由可简述为两点:一是法律上,《贷款通则》在法的效力层次上仅是部门规章,依照《合同法解释一》的规定,违反之不足以影响当事人间“贷款减免”合同的效力;二是法理上,违反监管政策的结果在于形成对监管对象的行政处罚,而并不会影响其对外与当事人交往的法律效力。
四、模式与操作
从前面制度层面梳理下来,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国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能否自主减免贷款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这种长期的冲突性局面使得商业银行对该问题无所适从,举步维艰,始终无法建立起良好的预期。但即便存在着合规风险,在实务中商业银行与债务人达成贷款减免协议的做法依旧屡见不鲜。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其背后实益。假使100万元的贷款出现逾期,银行几经追索,再经强制执行,仍系无果,颗粒未收。正当绝望时,若债务人提出“归还70万元,拗断剩余债务”之方案,试问银行是做还是不做?在聊胜于无的经济理性之下,商业银行又岂有不做之理。
一面有潜在的合规风险,另一面又有现实的迫切需求,商业银行在夹缝中究竟该如何自处呢?依照笔者的办案经验,并不存在可完全兼顾两者之贷款减免的操作方法,但能适当兼顾而比较保险的做法还是有的,即利息挂账。如前述,挂账是在会计上做停息处理,对债权本身没有实质影响,因而其在监管制度上有存活之空间。这亦是挂账与减免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商业银行正可利用该点作为与债务人谈判之起手式,唯在具体操作时,尚需讲究阶段、时机、模式及表达。
具体来说,《贷款通则》严格禁止商业银行对非不良类贷款做停息和减免的操作,但似乎对不良贷款网开一面,只禁减免未禁停息。所以,银行在与债务人协商还款方案,申请利息挂账时之贷款的五级分类应限定在不良类(次级、可疑或损失)。在操作时机的选取上,笔者建议要放在强制执行阶段,且是在全部执行程序到位仍无效果或能处理的财产已然变现时,再考虑与债务人商议部分还款方案。尽管在理论上,部分还款方案在贷款逾期后、起诉前、审理中、执行前等都可以提出。但在这些时点上,债务人之财产状况尚未经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之摸排与处理,债权银行无法对债务人之财产的数量与质量做出完整与准确的判断,若此时即轻易与债务人达成部分还款方案,未免过于草率,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债权。对于处理不良贷款的业务人员和清收人员来说,有了这一道强制执行程序的屏障,也能有效克服道德风险,形成自我保护。而就该类达成部分还款的贷款业务而言,也较禁得起事后的内外部审计。既然实务中的减免与挂账多采书面形式,而操作时机又选在执行阶段,那么执行和解自应成为当仁不让的首选模式。不过,在关键条款的语句表达上,挂账与减免并不相同。如采挂账操作,因不免除债权,在债务人部分履行的前提下,商业银行能做出的让步是“对剩余部分债务不再通过任何方式进行追索”。故,债务人主要取得的实际上是不再被债权人和法院打扰的权利。如采免除操作,则债权人给出的交换条件是“明确放弃部分债权”。利用执行和解的好处至少还有两点,一是执行和解往往系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需交由法院备案或记入笔录;该种正式感有助于债权银行与债务人建立彼此信任,同时敦促债务人自觉履行。二是但凡债务人未按约履行的,债权人可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做到进可攻,退亦可守。
五、对债务人之影响
减免和挂账两种操作方式对债务人之影响大不相同,这其实也应当成为债务人一方应事先了解的重要信息,以便提出对己最合适的方案。站在债务人角度观察,减免显然要优于挂账,是一种治本之策。但未必所有的银行都甘愿承受合规风险,拒绝部分履行之方案也属常态。此时,债务人即可考虑是否能提出银行方接受程度更高的挂账方式,换得债权人对已不再进行任何追索的勿扰模式。
依笔者前文建议,该债务和解的操作应放在债务人名下能处理的财产已经变现且全部执行程序到位仍无效果时,故本文所涉的债务人原则上仅指主债务人及保证人,不包括抵押人。又,银行债务中一般保证已几乎不见,所以这里的保证人实指连带保证人。具体说来,减免方式会给作为执行和解当事人的债务人带来以下影响:1、债务数量实际减少,还款义务减轻;2、履行后,主债务消灭,保证责任消灭;3、履行后不存在债务抵销之可能性;4、若执行和解的债务人仅有个别连带保证人,债权银行通过保证人的履行部分受偿了主债务,主债务在相同范围内减少,但并不消灭。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应在相同范围内减少,唯仍需对剩余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5、履行完毕后,法院应当删除其失信信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及基于债权银行之同意解除限制消费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6、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自履行完毕后5年,征信机构对个人债务人的不良信息应予删除。而除前述第5点外,挂账方式下的不同影响对照如下:1、债务数量没有实际减少,并按贷款合同之约定继续增加;2、履行后,主债务减少导致保证债务在相同范围缩减,但不存在主从债务彻底消灭的情形;3、履行后仍存在抵销依据及可能性;4、申请挂账主体只能是主债务人,故保证人不可能成为执行和解当事人;5、因债务未获免除,贷款不能获得正常结清,债务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上的余额不能清零,除非债权银行主动进行核销,否则其不良信息会一直留存;6、债权转让时,受让人取得的是未有任何免除的完整债权。债权银行当初在执行和解协议里做出的“对剩余债务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索”的承诺对受让人并无拘束力,此点对债务人尤其不利。
而无论是挂账还是免除,就银行征信而言,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征信业管理条例》仅规定了个人债务人不良信息的删除条件,对非自然人债务人的不良信息能否删除语焉不详。依照目前行业惯例,若债务人系非自然人的,其不良信息一旦产生,需做永久保留,不得删除。二是在不良信息保存期内,若债务人另有他行融资需求的,债权银行可以综合考虑债务人的违约情节、还款意愿、履行情况等因素提出书面说明函,以帮助债务人提高获得他行融资的可能性。反过来看,这一点对债务人亦存在足够吸引力,可以成为债权银行谈判之筹码。
六、总结与反思
作为商业银行来说,在许多业务问题的处理上,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如何妥适地解决坚守合规底线和维护商业利益这一矛盾。债务和解问题亦是如此。在不能全额收回贷款本息的条件下,银行欲与债务人进行债务和解时,可以选择债权减免或利息挂账的操作方式。综上分析,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从商业银行的立场出发,具体方式的选择一方面要确保相关操作符合当前监管规定,另一面又需适当满足债务人之利益,换取其配合以达到受偿部分债权之目的。相较之下,笔者建议债权银行优先尝试挂账方式。实务中,在某些重大的债务重组或债务和解过程中,亦会出现政府机关或监管部门主动介入,呼吁甚至要求各商业银行给予债权减免的情形。此时,因存在公权力背书,减免操作未尝不可。但倘若要从根本上消除减免方式所带来的合规风险,只有依靠《贷款通则》之修正。笔者也借此文呼吁,期望监管政策能及早归位,与《商业银行法》对此问题的立场保持一致,真正地为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免操作减压松绑。